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一本最近文化圈热议的82.5万字《龙泉山传》,以山体拟人化的灵魂三问开篇,打破了山岳写作的传统范式。作者凸凹用32年光阴沉淀情感,24年时间实地踏勘与笔耕不辍,将北起绵阳安州、南止乐山五通桥,纵贯5市28区县的龙泉山脉,从“成都人的农家乐”还原为“天府万古脊梁,巴蜀硬核地望”。这部中国首部山岳传,既是地理志、人文史,更是一场人与自然的精神对话,让一座沉默的山脉,成为承载巴蜀文明的鲜活载体。

凸凹,本名魏平,1962年生于都江堰,1993年初随航天062基地调迁移居龙泉山下,与这座山结下32年不解之缘。他的写作横跨小说、诗歌、散文、非虚构等多个领域,作品兼具史料严谨性与文学感染力,此前著有《甑子场》《大三线》等多部聚焦地域文化的力作。在《龙泉山传》中,他延续了对巴蜀文化的深耕,却突破了传统方志的书写局限,构建出独特的叙事体系。
“没有龙泉山脉就没有成都平原,而没有成都平原就没有天府之国和成都。”凸凹在书中抛出的这一论断,颠覆了许多人对龙泉山的认知。在他看来,这座被不少人视为“看桃花、打麻将”之地的山脉,实则是川西平原与川中丘陵的界山,岷江与沱江的分水岭,更是巴蜀文脉的重要载体——从鳖灵治水到李冰开渠,从三苏文脉到三线建设,无数历史印记镌刻其上。
凸凹对龙泉山的情感,早已超越地理归属,升华为精神图腾。“家父葬于龙泉山脉主峰长松山已18年,家人18年的上山下山,让龙泉山成了我家事实上的‘香火山’。”他在采访中直言,自己早已在诗中留下遗言:“死后不仪式,不筑墓,不立碑,将一把骨灰抛撒在龙泉山即可。”这种深度羁绊,让他的书写既有田野调查的扎实,又有精神共鸣的温度。
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跨文体非虚构”的创新尝试——融合散文、诗歌、纪实、评论甚至小说、戏剧元素,同时采用双第一人称叙事:一个“我”是作者,一个“我”是山体。“‘山体的想象’中的核心部分,恰恰对位了‘史料的严谨’,我用形式上的大虚构,完成了事实上的硬核非虚构。”凸凹这样阐释其写作逻辑。书中仅“山”“峰”“坡”等山岳相关词汇就出现9400次,却无刻意堆砌之感,足见其对山脉精神的深刻体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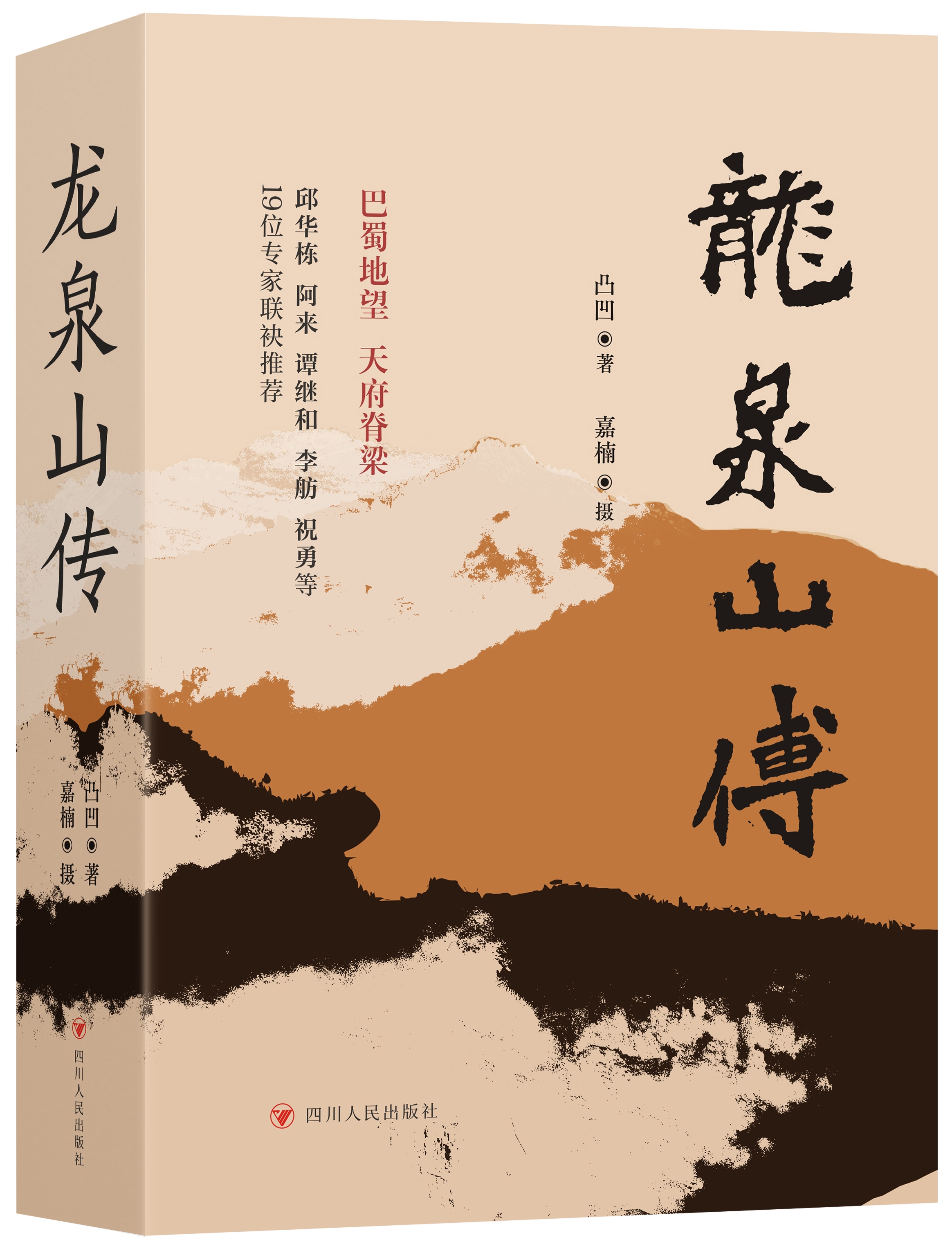
●“那一刻,我动了念头,要把龙泉山脉写出来”
◎读者报:凸凹老师,您在《后记》中提到,您与龙泉山的羁绊已延续32年,您更是将其认作“事实上的家山”。我们很好奇,在这32年里,是否有某个具体的瞬间,让您突然意识到“我必须为这座山写一本书”?这个“立传”的念头,是偶然触发,还是长期情感积累的必然?
凸凹:在写《龙泉山传》之前,2001年至2004年间,我已写过一本书,叫《花蕊中的古驿》(成都时代出版社2004年11月),8万余字。这本书的一部分内容,事实上已成为《龙泉山传》之龙泉山脉龙泉驿段的部分半成品文字。但当时,我并不知道,书中文字20年后会有一个蜕变似的重生。那时,我对龙泉山的认识,还处于没有发蒙的阶段。
现在回想起来,为龙泉山立传的念头,是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的。说来也巧,那个念头,距今刚好十年。那是2015年6月6日,一个周六的上午。
应乐山文化人孙雁鸣邀,6月5日午后,我和诗人印子君从龙泉驿自驾到了乐山。热情的雁鸣兄呼朋唤友,当晚就在三江坝子举办了一个七八人的诗酒聚会。男男女女的风雅颂,高过了岷江、大渡河和青衣江的风声、浪头。
一觉醒来,残酒未尽,雁鸣兄就带我和子君去紧邻乐山大佛的江边喝茶唠嗑。我知道龙泉山脉的南缘终端在乐山市市中区境内,但不知具体在哪里,就向雁鸣兄请教。他遂指着点着河对岸的一脉山物介绍说,它们是凌云山、乌尤山、龟城山、九峰山,龙泉山脉的终点地区应该就在这一带。闻言,我惊得目瞪口呆,虽半信半疑,依然大喜过望。果如此,乐山大佛就寓于凌云山体内,而恭恭敬敬虔虔诚诚托起乐山大佛的凌云山不就是龙泉山脉的龙头吗,名遐天下的乐山大佛,不就是龙脸吗?那一刻,我动了念头,要把龙泉山脉写出来,立在纸上。我知道这个念头背后落地的干活儿的难度——倘若不难,从古至今,那么多写手,那么多天纵之才,早把龙泉山脉的开山之作呈现于世了。
既然难,那就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
返回龙泉驿长松山下,6月12日至13日,我写出的百行长诗《龙泉山志》,算是对那个上午的惊喜与神启给出了自己的回应,也给出了龙泉山脉最高峰长松山的态度:“逐龙而居的人走到了语言的尽头,思想的尽头/……大佛其实更是一条巨龙的龙头/从安县把头伸过来,饮乐山的水”。
7月2日至4日,从龙泉山脉的一个偏旁,写了几千字的散文《从诗歌的方向登临龙泉山》。
初秋,我在大型文艺季刊《龙泉驿创作》(后更名《龙泉山》)2015年第三期(秋季号)以专题形式隆重推出“龙泉山脉诗群”大展。长约300公里、沿山区县多达20多个的地界上的135位诗人,首次以一脉山的名义抱团参展。这也开了有史以来以整体龙泉山脉为地域搞活动的先河。
次年,秋,在我的提议下,《龙泉驿创作》更名为《龙泉山》。我为这期(2018年第3期)写的卷首,名为:从龙泉山,到龙泉山——写在《龙泉驿创作》更名《龙泉山》之时。
由此可以看出,自有了6月6日那个念头后,我的视域与笔触,不再局限于成都主城区东边的那一小截龙泉山,而是放眼整条山脉。就这样,我逐渐走上了为龙泉山脉立传的路。
但把为龙泉山脉立传的活儿干成《龙泉山传》的样子,却不再是一个念头,而是需要一个偶然又必然的机遇——对龙泉山脉多年的抚摸以及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的设立与建立形成的强大气场,对周遭的物事有着风吹草动、见微知著的影响。
机遇来自2023年3月3日,傍晚,龙泉山顶“本原”民宿。一众文朋诗友卿天,就从自然的实体龙泉山聊到了纸上的尚属子虚乌有的龙泉山,就聊到了我。而我的老朋友,一上任就热衷于编龙泉驿区文史资料,正愁2024年度选题还没着落的龙泉驿区政协文史委主任刘学伟身置“场”中,当场兴奋不已,对龙泉山脉选题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正是这一极大兴趣,变成了我又爬山又爬格子的行动。而我的行动,于2024年底让龙泉山脉变成了文史资料《我是龙泉山》(内部资料)。而龙泉山脉文史资料的价值,又让四川人民出版社看到了公开出版龙泉山脉的社会效益——2024年5月13日签出版合同,2025年天府书展开幕前夕《龙泉山传》面世。
◎读者报:您出生于都江堰玉垒山下,长于万源县花萼山下,最终落脚龙泉山下。这三座山在您心中的分量有何不同?为何偏偏是龙泉山,让您愿意投入24年时间完成这部82.5万字的“山岳传”?“家山”这个概念,对您而言,是地理归属,还是精神图腾?
凸凹:简而言之,三山相较,客观上说,龙泉山更大、更重要——更值得写;主观上言,龙泉山给予我的经历、苦乐和存在感更丰饶——我今年63岁,与她生活在一起已历32年之久。先父于汶川地震前一年过世,葬龙泉山脉主峰长松山已18年。家人18年的上山下山,已让龙泉山成了我家事实上的“香火山”。
因于此,“家山”这个概念,于我既是地理归属,也是精神图腾。写完《龙泉山传》后,竟有一种莫名的殚精竭虑的解脱与空无。于是,我又用一首名《清音溪》的诗写下了我的“遗言”:死后不仪式,不筑墓,不立碑,将一把骨灰抛撒在龙泉山即可。万物出于山,从于山,自当归于山。
 ▲龙泉山美景(何建/摄)
▲龙泉山美景(何建/摄)
●“行走山中,让我意外的经历颇多”
◎读者报:您在书中提到,为了写《龙泉山传》,您几乎登临了龙泉山脉所有高峰(长松山、老牛坡、丹景山、玛瑙山等),钻过老林、探过溶洞,甚至叩访过“地面的、地下的”人。在这趟跨越5市28区县的踏勘中,哪一次经历让您最意外?比如是否发现了史料未载的遗迹、听到了颠覆认知的民间传说,或是遇到了让您重新理解“山性”的人和事?
凸凹:行走山中,让我意外的经历颇多,比如在眉山市东坡区富牛镇永光村遇到苏洵家族墓地,比如从李调元故里去玄武山因走错路,竟误打误撞去了中江县集凤镇,见到了台湾诗人覃子豪的纪念馆和龙泉山少有的溶洞群。
史料未载或记载模糊的遗迹很多,比如那些新发掘出的文物:龙泉驿战国墓、北宋山水画家高克明墓……
听到的民间传说中,颠覆认知的谈不上,但让我震惊的还是有的。比如,龙泉山守碑人肖太发老人给我讲的民国时期发生在石佛寺的有关尼姑、“北洋大汉”、阔少、刘和尚以及蟒蛇的故事。
为突出山性,我在书中密植了频次极高的几个词,创下了一部书之最:“山” 7143个、“丘” 179个、“峰” 298个、“坡”443个、“高”1157个、“海拔”180个,总计9400个。这个数据,写作时却是不知不觉,顺其自然,毫无违和感的。
凡落居在山区的人和事物,皆浸淫、附体有山的脾性、特性和气息,也就是我说的“山性”。而我在龙泉山中遇到的那么多历史名人的墓况,却让我对山性的理解变得更加迷茫、复杂和难以言说。比如,涪城西山名臣蒋琬阴宅豪华的样子,老泉山苏轼兄弟生父生母苏洵、程夫人和苏轼发妻王弗在山中抱团守望的样子,学人王叔岷、蒙文通安寝龙泉驿公墓的样子,才子李调元独自一人待在老家的样子,而一代名将岳钟琪筑在松秀山地层里的宅子早已荒凉成穿风走雨的茅屋的样子……
◎读者报:李忠东老师在《跋》中说,龙泉山曾是“成都人的农家乐”,很多人对它的认知停留在“看桃花、打麻将”。您在踏勘中是否也遇到过这种“认知偏差”?比如某处被忽视的古驿道、某座被遗忘的古寺,您是如何通过实地走访,挖掘出它们背后的“地脉与文脉”,让龙泉山从“物质之山”回归“精神之山”的?
凸凹:忠东兄说的很多人对龙泉山的认知偏差,我看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对龙泉山脉地区范围的界定。很多人知道的龙泉山只是成都主城东面的那座山,长不过几十公里,宽不过一二十公里。《成都市金牛区志》(1996)载:“龙泉山脉分支凤凰山、天回山、磨盘山、塔子山、狮子山和东山浅丘带盘绕(金牛区)东北边缘。”他们哪里知道,连成都城东北二三环一带都属龙泉山西麓铺衍的地盘,其分支磨盘山更是成都主城区海拔最高的地方——换言之,耸立在成都主城区的最高峰是龙泉山。事实上,龙泉山脉长约300公里,宽约30—70公里。这个尺度和体量覆盖的古今事象,农家乐、桃花和麻将自是扛不住的。
二是对龙泉山脉的地理位置和之于成都平原的认识不足。事实是,没有龙泉山脉就没有成都平原,继而成都,继而天府之国。
三是没有将史籍文献的记载和诗文,与龙泉山脉对位。一旦对位,就会发现,自古诗人例到蜀,到蜀必到龙泉山。还会发现,其山的文脉是与巴蜀地区的文脉“相如赋,太白诗,东坡词,升庵科第”同频共振、一脉相承的。
拨正了以上的信息偏差,就没有了认知的偏差。
“天府万古脊梁,巴蜀硬核地望”,正是龙泉山脉从物质之山到精神之山的纵横写照——没有为龙泉山脉立传的经历,提炼不出这个写照。

▲《龙泉山传》研讨会现场
●“我这叫诚实、公开、名正言顺的虚构”
◎读者报:您提到书稿中“除龙泉驿段部分旧稿改写,其余全为新撰”,且单篇《孤茅压众山——隐身龙泉山的隋唐名士朱桃椎》就写了1.9万字。面对“史料碎片化、残影杂乱”的难题(比如朱桃椎的生平记载极少),您是如何通过“故事链”串联细节,让历史人物和场景“活”起来的?这种“以小见大”的写法,是否是您刻意选择的叙事策略?
凸凹:你能提到《孤茅压众山》,我倍感欣慰。全书只有这篇我是尽着性子写的,完全没有顾及篇幅体量什么的。
写非虚构作品,各人有各人的“刀法”。但不管使用什么“刀法”,都是要将史料、时间、空间、人物、传说、踏勘、访谈等“碎片”,用一根链子串起来,建一个自己初设的理想中的模。我为《龙泉山传》建模的“故事链”是独有的龙泉山脉。比如,把这条链子用在《孤茅压众山》上,我是让龙泉山脉的茅、草编、道教和彭山薛稷为朱桃椎画像、唤魂,直到仿真复盘。
将整体剖零,再“以小见大”,从一滴露水中见太阳,可以认为是我刻意选择的叙事策略。但不这样行吗?物理学的“压强”告诉我,以大探大,要么破灭,要么进不去。
◎读者报:《龙泉山传》最独特的一点,是采用了双第一人称叙事——一个“我”是作者,一个“我”是山体。比如开篇就让龙泉山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种拟人化的“山体视角”,会不会让非虚构写作面临“真实性”的争议?您在写作中如何平衡“山体的想象”与“史料的严谨”?
凸凹:不会。因为“山体的想象”中的一些核心的貌似虚构的想象部分,恰恰对位了“史料的严谨”。换言之,我用形式上的大虚构,完成了事实上的硬核非虚构。
我这叫诚实、公开、名正言顺的虚构。毁坏真相、真实的罪魁祸首是隐瞒的撒谎式虚构,比如虚构散文——就是用谎言消费读者感情,让人上当。

▲在2025天府书展主会场举行的《龙泉山传》新书分享会现场
●“这就是我‘文体混搭’的目的”
◎读者报:阿来老师在《序》中提到,您的写作融合了布罗代尔的“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地理时间写自然演化,社会时间写人文历程,个人时间则是您的踏勘与思考。比如书中龙泉山“植物志”“动物志”章节,用科学的博物学视角记录草木鸟兽,又穿插您与护林员、摄影师的互动。这种“科学与人文的交织”,是不是对传统非虚构写作的突破?您为何要花大量笔墨写“植物、动物、地质”,而不只是聚焦历史与文化?
凸凹:这种“科学与人文的交织”,是不是对传统非虚构写作的突破,突没突破,我不知道,还是留待评论家说。
为山岳立传,写的对象是山,就得在时间的长轴上,花大量笔墨,把山的组成板块写完全,写透彻。地下的岩,岩上的土壤,土壤上的动植物,动植物上的空气、天象、季候,都得花大量的时间,整理清楚,一一写来。
动物中的高级的一类,就是人类了。“山,宣也,宣气散,生万物……凡山之属皆从山。”(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山生万物,人是万物中的一物,自然也是山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的体量和重量占比不大,但能量和动作却是超大的,没有更多的文字给出,是框不住人类的。因此,写山岳传——写给人看的书——人文也是重头戏。
《龙泉山传》通过四川人民出版社终审后,黄立新社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大部头可是一部百科全书啊。”黄社长的意思是,这本书涉及的学科门类较多。我学的混饭吃的专业是工科(机械制造),先后在航天工厂干过设计所设计员、工艺处规划员,在《四川航天报》当过编辑记者,在062基地下属公司做过法定代表人,下海重庆任过某私营公司总经理。从2001年起,在地方文旅局、文联上班直到退休。
这种“吃得杂”的经历与经验,与生万物的山岳,可谓气味相投。所以,你所言的花大量笔墨写“植物、动物、地质”,而不只是聚焦历史与文化,且体量达82.5万字的《龙泉山传》,在我看来,还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部山岳传。美国人德怀特·康斗·贝克尔撰写的《泰山传:东岳圣山志》(商务印书馆1925年)的体量仅为《龙泉山传》的八分之一。我相信,从“百科”的扇面为一座大山老老实实立传,几万字的编织与码垒,是根本办不到的。
◎读者报:您在《后记》中说,这本书是“跨文体非虚构”——融合了散文、诗歌、纪实、评论,甚至小说、戏剧元素。比如写“三国故事”时,您会用场景化的语言还原战场,写“客家迁徙”时,又会插入民谣与民俗细节。这种“文体混搭”的目的是什么?是否担心读者会觉得“杂乱”?您心中理想的“非虚构文体”,应该具备怎样的弹性?
凸凹:创作即创造发明,即便是非虚构写作,也应该有创造发明的意识。这种意识甚至可以严苛到不允许自己抄袭自己。就是说,哪怕仅从文体学、文本学的视野看,你的作品,就是你的作品,而非别的什么人的作品。创造发明独属自己的文体、文本的方式之一,就是对各种文体进行排列组合般的多种重构。这就是我“文体混搭”的目的。
我不会担心读者会觉得“杂乱”。因为我四十年的创作实践,证明我有融合散文、诗歌、纪实、评论,甚至小说、戏剧元素的能力——那种丝滑穿梭、自由出入的能力。
让“非虚构文体”与“弹性”勾连,我觉得你用得很妙。至于在我心中理想的弹性应该具备什么,我认为应该具备减震性、抗压性、反弹性、吸纳性和包容性,也就是龙泉山脉山西成都平原的地质特性——冲积平原。而制造“非虚构文体”弹性的最佳途径正是多文体的加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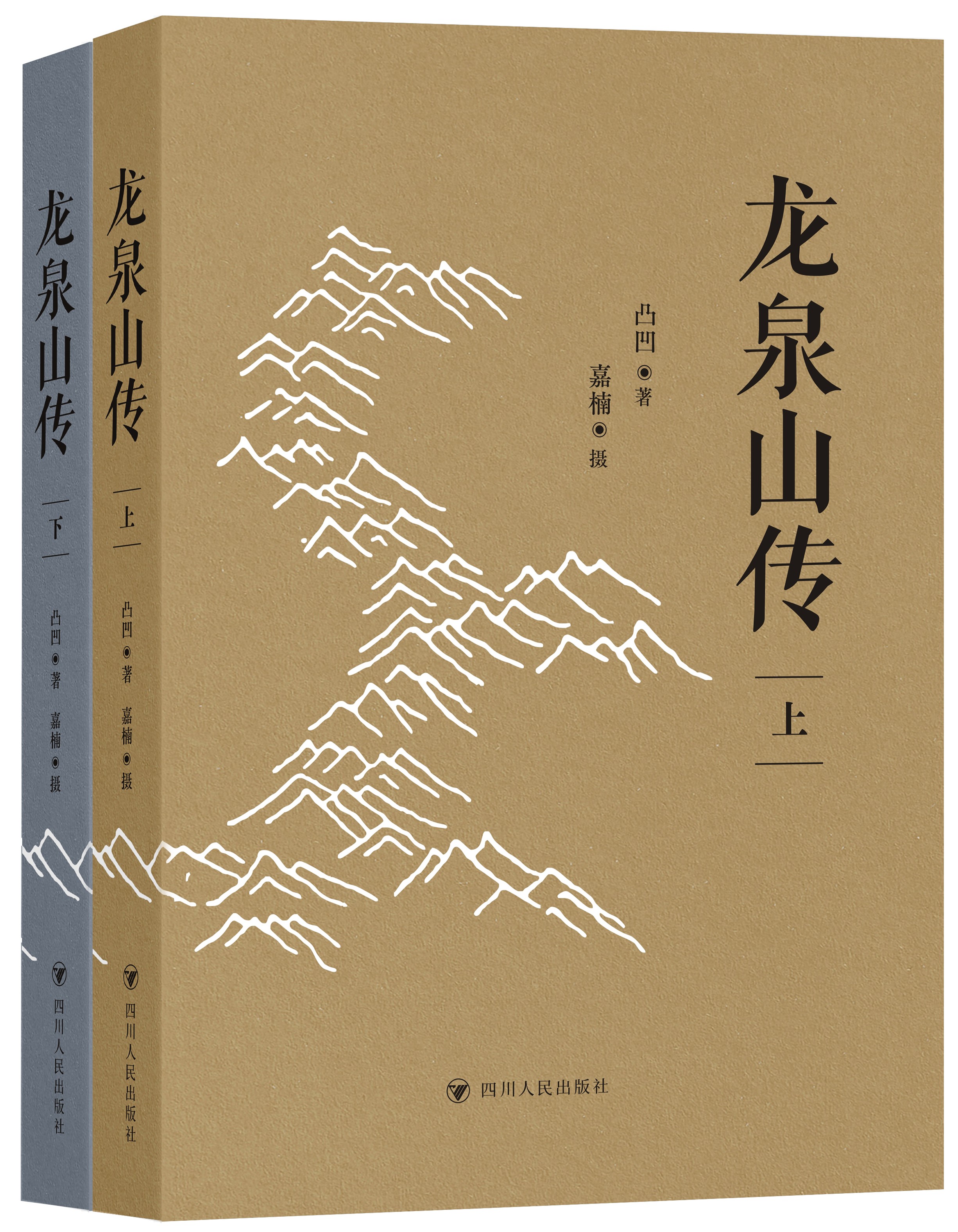
●“目前游历龙泉山脉做攻略的唯一指南”
◎读者报:谭继和老师评价这本书是“第一本龙泉山地脉水脉文脉错综会通于巴蜀的杰作”,书中既写了古蜀文明(蚕丛、李冰)、三国历史(庞统、张飞),也写了现代场景(天府国际机场、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丹景台)。您如何看待龙泉山的角色转变——从过去的“成都东部边界”,到如今的“城市绿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地望”?书中哪些章节最能体现这种“时代变迁”?
凸凹:龙泉山脉从古至今的角色转换,我以为这要归于她是一座离人气很近的山,这也意味着她是一座文明化程度极高的山。这样的山之变,就像甲骨文时代变AI时代,属于世界之变的一部分,正常。而那些离人类高远的雪山,则变得少而慢,仿佛静止在那里。
书中最能体现这种“时代变迁”的章节,是《龙泉山动物志》《巴蜀古驿道,成都东大路》等。
◎读者报:您在书中提到,龙泉山是“可以拿来用的山”——望雪山、拍飞鸟、住民宿、探溶洞,已成成都人的生活潮流。但同时,您也在挖掘它的“精神意义”,比如欧阳修出生地、苏轼的“老泉山人”自号、杨升庵的文脉传承。在您看来,当代人对龙泉山的“休闲化消费”与“精神性认知”,是否存在矛盾?这本书能否成为连接两者的桥梁?
凸凹:不矛盾。正像高密度物质总有向低密度物质流动的本能与能量一样,人也有从高密度人群向人烟稀少地带流动的渴望与频率。当代人从大都市成都上龙泉山的“休闲化消费”,既是物质层面稀密度调和的自然规律,又有精神层面的对宇宙、世界和人生认知不断调整与升级的在地变现。换言之,工作劳累换来的财富在支撑基本生活后所溢出的部分,是需要快速、就近地在龙泉山“休闲化消费”中用“精神性认知”去冲抵与平衡的。
我说过,没有什么问题是上一次龙泉山解决不了的。对成都而言,连接“休闲化消费”与“精神性认知”的桥梁肯定不止一座,但《龙泉山传》一定会成为最重要的一座。《龙泉山传》是研究、发掘龙泉山脉的母本,更是目前游历龙泉山脉做攻略的唯一指南。
 ▲“凸凹新书《龙泉山传》走进金堂分享交流活动”现场(薛向阳/图)
▲“凸凹新书《龙泉山传》走进金堂分享交流活动”现场(薛向阳/图)
●“我采用了最朴白、简约、直接的文字”
◎读者报:书中专门写到“三线建设”对龙泉山的影响——您自己就是航天062基地调迁人员,这段经历是否让您对龙泉山的“工业记忆”有更特殊的情感?您在写“三线企业”“航天城”时,如何避免写成“史料罗列”,而是让“工业文明”与“山水文脉”产生共鸣?
凸凹:我16岁进入三线航天,39岁调离,这样的经历,对龙泉山的“工业记忆”自有一种更特殊的情感,也有一种更深切的认识。
囿于体量,不能随性写,这一章节我虽做了避免写成“史料罗列”,而是让“工业文明”与“山水文脉”产生共鸣,但做得并不理想。
◎读者报:您说《龙泉山传》的“最低托底界岭”是“成为龙泉山脉百科全书的目录或索引”,这种“谦逊”背后,是否藏着您对“山岳写作”的敬畏?毕竟这是“中国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山岳传”,您是否担心自己的书写“不够全面”?或者说,您认为“为山岳立传”的核心,不是“穷尽所有”,而是“照亮某部分被遗忘的角落”?
凸凹:我的心思,你都猜中了。
为了控制体量,我采用了最朴白、简约、直接的文字,尽可能避开形容、修饰、闲笔、蹈空想象,少发感想,少做评论。即便如此,还是达到了上下两册共82.5万字的体量,定价还是冲到了168元的“高位”。
从头到尾,我都是“忍”着撰,“压”着写。约略放开写的只有2个章节:《孤茅压众山》和《龙泉山动物志》。书中用到了诗,因为诗最节省字。
◎读者报:当下“城市传”方兴未艾,但“山岳传”仍属稀缺。您认为《龙泉山传》能为后来的“山岳写作”提供哪些启示?比如“在地性”的重要性(必须扎根山脉、深入民间)、“多学科视角”的融合(地理、历史、生态、民俗),还是“个人情感与公共价值的平衡”?
凸凹:你说的启示,应该都存在。但体量、定价与市场发行的问题,也得考虑。再一个启示,应该是整书结构以及叙事人称和角度。《龙泉山传》中的“龙泉山大事记”,我认为也算一个特色和发明。
 ▲龙泉山美景(何建/摄)
▲龙泉山美景(何建/摄)
●“大家终于知道龙泉山脉原来这么迷人”
◎读者报:作为长期深耕巴蜀文化的作家,您之前写过《甑子场》《大三线》等作品,未来是否还会继续关注“地域题材”?《龙泉山传》之后,您与龙泉山的故事是否会继续?比如围绕书中某个未展开的细节再做深入挖掘?
凸凹:我首先会完成一部长诗《山房子:龙泉山脉诗传》的写作与出版。
之后,围绕书中某个未展开的细节再做深入挖掘,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事实上已有考虑,但具体选题,保密。
◎读者报:作为“龙泉山的代言人”,如果让您给读者推荐一条“读懂龙泉山”的路线——不是旅游攻略,而是“文化探访路线”,您会选择哪几个关键点位(比如长松山蚕丛庙遗址、石经寺、丹景台)?为什么这几个点位能串联起龙泉山的“前世今生”?
凸凹:依从时间的大致流向,我推荐的访古之路为:彭山彭祖山、长松山蚕丛庙遗址古银杏、鳖灵峡、江口古街、涪城西山、鹿头山白马关和庞统祠墓、金牛区凤凰山、龙泉驿天落石北周文王碑、龙泉驿金龙寺、牧马山之象耳山、三台琴泉寺和牛头山、中江玄武观、平羌峡、锦江山太白亭、金堂三学寺、乐山大佛和乌尤寺、仁寿牛角寨大佛、成华区磨盘山、云顶山、东部新区丹景山顶峰佛兴寺、甑子场、青神中岩山、东坡区蟆颐观和苏洵家族墓地、井研三江白塔、虞允文墓、东坡区白塔山、石经寺、五通桥四望关、黄龙溪古镇、五凤古镇、金堂天星洞、岳钟琪墓、鹡鸽寺、罗江醒园、雷氏民居、锦江区狮子山、贺麟故居。
这几个点位能串联起龙泉山的“前世今生”,总体上讲,是因为它们有历史、有人物、有故事、有山性,尤其还有真身可供抚摸、合影。有些点位,早已消失于时间的长河,无迹可寻。
◎读者报:一座山在不同的人心中有不同的颜色,在您心中龙泉山是什么色?从古至今写成都的书大大小小恐有几百上千本之多,但写整体龙泉山脉的书只此一本,这是为什么?如果你没有写,你估计还有多久才会出现龙泉山脉的开山之作?现在,您写了,会不会出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情况?
凸凹:地处成都平原东侧的龙泉山脉,在我这里的颜色永远都是紫色,紫气东来嘛——吉祥之气之色丝丝缕缕来自东山。
从古至今写龙泉山脉的书只此一本,原因很多,主要为:一是对这脉山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认为这座山太小、太矮,山形山势太平庸——可知为欧洲、亚洲划线的界山乌拉尔山脉,平均海拔也只有500—1200米;三是有写作的难度与人才,却无写作的情怀与机遇。
我如果没有写,估计还有多久才会出现?这个不好说,少则几年,多则几十上百年吧。现在我写了,出现了“前无古人”的情况,断不会出现“后有无来者”的情况——因为大家终于知道龙泉山脉原来这么迷人!

●采访手记:一座山的“百科全书”与一个人的精神修行
拿到《龙泉山传》时,最先被其厚重的体量震撼——82.5万字,上下两册,配图300余幅,附录1.2万字的《龙泉山大事记》,难怪专家称之为“一部百科全书”。采访凸凹先生时,他言语间对龙泉山的熟稔,仿佛在谈论自己的家人,那些山脉的走向、古迹的位置、传说的细节,信手拈来,背后是32年的陪伴与24年的深耕。
凸凹的写作,打破了“山岳传”的稀缺局面,更重构了地域写作的范式。他没有局限于历史史料的堆砌,而是用双脚丈量300公里龙脉,叩访“地面的、地下的”人,将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熔于一炉。书中既有科学的博物学视角,记录草木鸟兽的生态变迁;也有人文的深度挖掘,还原古驿道的文明脉络;更有个人的情感共鸣,让“家山”成为精神的归宿。
最动人的,是他对“山性”的探寻与呈现。在他笔下,龙泉山不仅是地理的存在,更是精神的载体——那些历史名人的墓况、民间守碑人的故事、三线建设者的足迹,都让“山性”变得立体而鲜活。正如他所说,“凡落居在山区的人和事物,皆浸淫、附体有山的脾性、特性和气息”。
《龙泉山传》的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龙泉山脉整体书写的空白,更在于搭建了一座桥梁——连接起当代人对龙泉山的“休闲化消费”与“精神性认知”。当我们再上龙泉山,望雪山、拍飞鸟、住民宿之时,或许能通过这本书,读懂脚下土地的文脉传承,感受这座“天府脊梁”的精神力量。而这种对地域文化的敬畏与深耕,正是当下稀缺的写作态度,也是凸凹先生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王欣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


天府书展|当阅读走出书页,“安逸四川”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天府书展|三地联动、微剧破圈!“文化名家采风行”启幕,四川文旅融合探索新范式

天府书展|阿来与乔叶,带我们走向诗与远方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