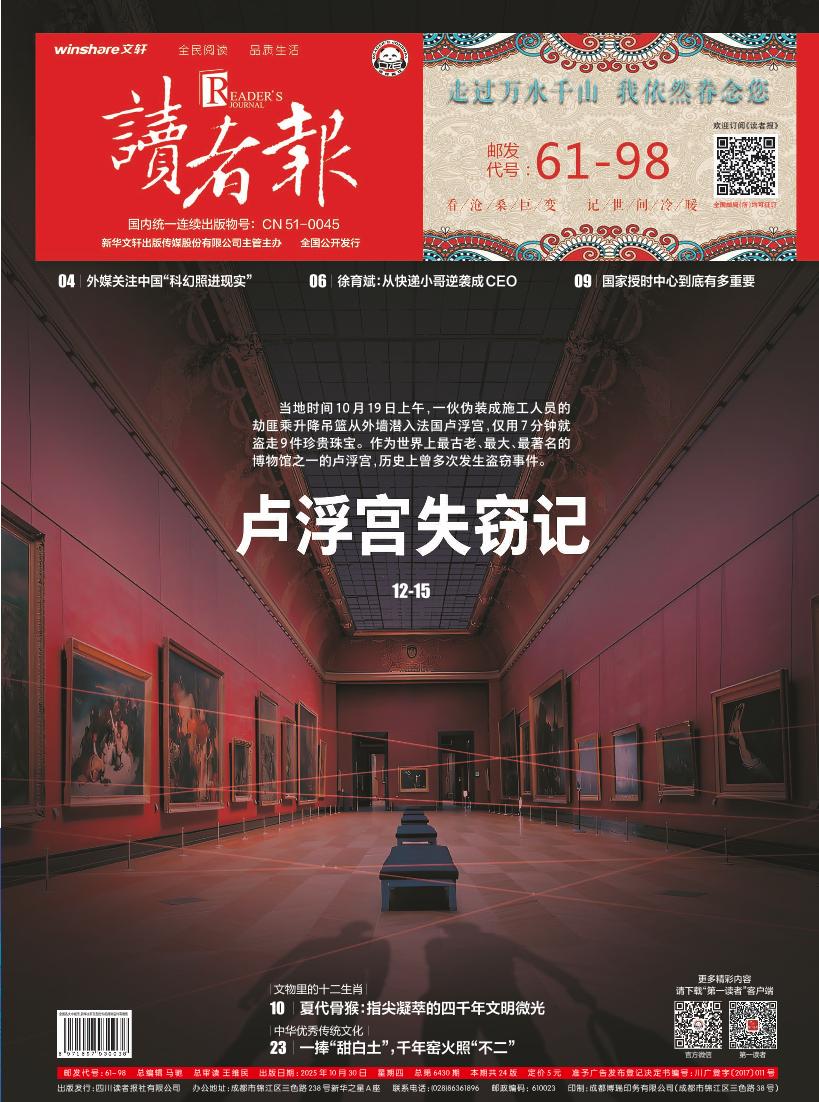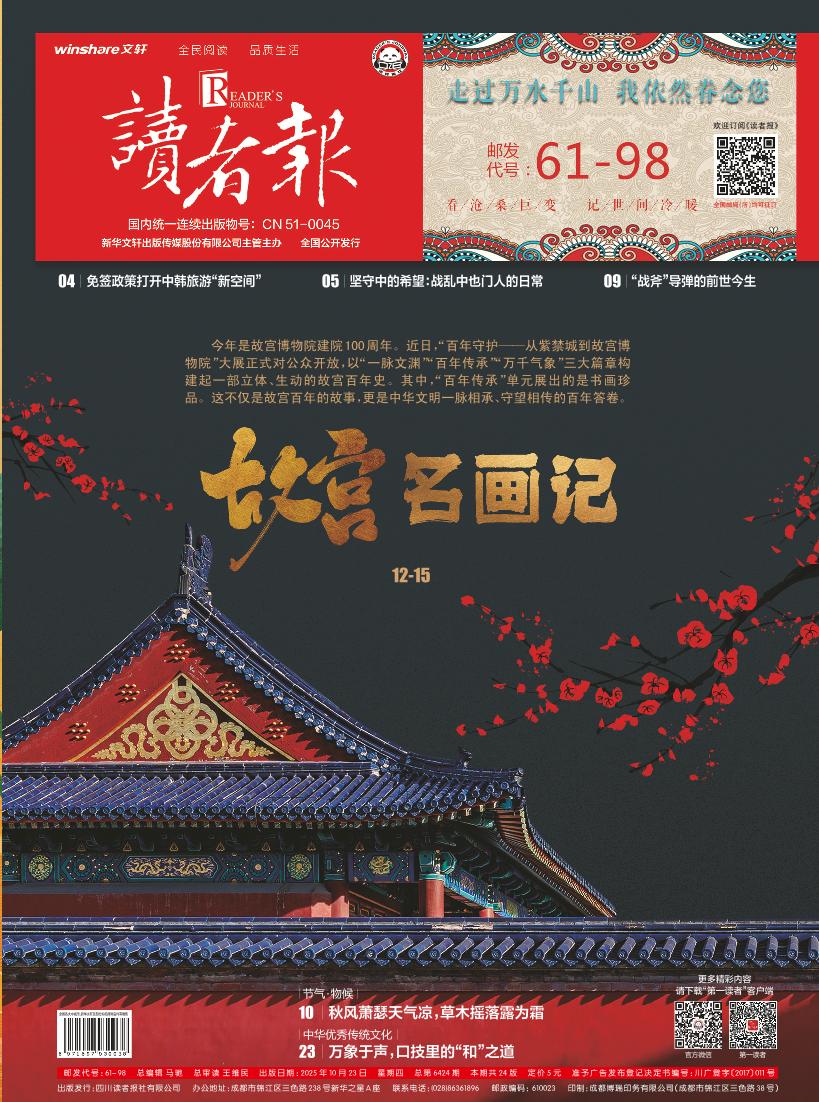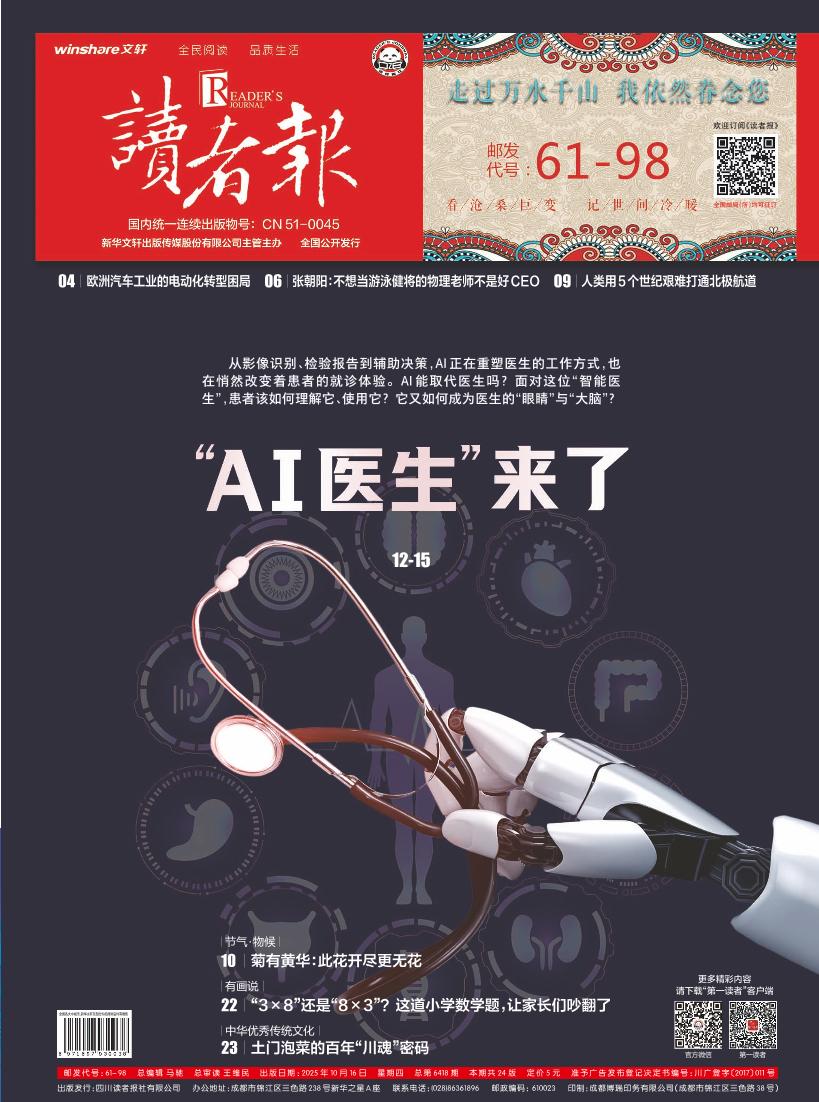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在当代的散文书写中,对一种“观看”的伦理的深度实践,最能体现作家的人生阅历、写作功底、审美境界,作者如何理解和看待自己的人生与大千世界的关系,决定了他理解、书写世界的方式,杨明强先生的散文集《老屋和炊烟》,便为此提供了一个极为独特且深刻的范本。杨明强拥有作家、摄影家与资深媒体人多重身份,其40年媒体与教育生涯和18年主编经历,锤炼出一种对山川风物、生活细节近乎本能的敏锐“凝视”。他习惯于在新闻现场般的现实生活中捕捉真实,而摄影家的身份,则赋予他一种对构图、光线和一处处决定性瞬间的精准把握。
因此,要真正读懂《老屋和炊烟》,必须引入一种“摄影化诗学”的批评视角,杨明强的笔,在很多时候就是他的镜头,这部集子不仅是作为杰出作家的杨明强的心血结晶,更是他作为一名优秀记者、优秀摄影家的,一部由光影、焦距和时间共同完成的“文本摄影集”,其诗学实践循着三条清晰的路径展开:以“观景器”向外框取天涯,以“暗房”向内显影故土,最终以“焦点”对准他者,定格人间。
以光影“框取”天涯
摄影,首先是框取。杨明强散文中的“行走”主题,尤其是第三辑“天涯羁旅”与第四辑“走读报告”,便是他将笔触化为“观景器”,在万里河山中框取光影与诗意的明证。他笔下的风景,总是在摄影师般对光线变化的精准捕捉中,赋予了深厚的诗意。
在《走读突尼斯》一文中,他描摹地中海的日出,其文字的运动轨迹宛如一台延时摄像机:
“天空的鱼肚白渐变成了淡紫、微红、灰蓝、金黄——这些不同的色彩, 有如调色板的巧妙布局。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推移, 渐渐地, 一轮崭新的红日, 拖着一缕缕橙色的海水, 缓缓地跳出海面。”
这种动态的记录关心的不仅是“是什么”,更是“如何变化”:“渐变成”“一秒一秒地推移”“缓缓地跳出”,这些细腻的词汇精准地复刻了“黄金时刻”光影流转的全部过程,当光线最终“由弱变强”,银白的沙滩变为“金色的沙滩”时 ,我们读到的,仿佛是一位大师级摄影师在凌晨的寒风中,为等待最佳光线而屏息凝神的全部耐心与专注。
这种对“视觉”的极致追求,最终会溢出视觉本身,通向更饱满的诗学感知。在《打卡斯里兰卡》中,他写道:“在视觉的冲击下, 我的嗅觉也敏感起来, 海风的咸味、植物的清香, 真是沁人心脾。”观看,成为了开启一位杰出作家全身心诗意的钥匙。
当杨明强的“观景器”框取到一个完美的画面时,媒体人的深刻洞察力便会瞬间介入,从而赋予画面以丰沛的哲思和高水准的审美。同样在斯里兰卡,他乘坐“海边小火车”,那梦幻般的场景最终在他的观景器中定格为一个深沉的隐喻:“看来, 人生也就像坐火车。火车走走停停, 旅客上上下下、去去留留, 有些人与你一见如故, 有些人与你相伴同行。你还不知道, 谁会陪你走完最后的征程……”这种由景入哲的升华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行走一天畅享四季》中,他更将达古冰川一日的气候变化与山川外貌,同“一年四季”巧妙关联,将视觉框取升华为对时空循环的哲思。
从北非突尼斯的异域奇景,到雪域高原达古冰川的变化风云,杨明强笔下关于“行走”的文字,是他用镜头般的妙笔去“构图”世界的成果,他是导演,是艺术家,是诗人,也是哲人,他的视线在哪里框定,无限的诗意和哲理就在哪里生成。
用时间“显影”故土
如果说“行走”主题是镜头向外的捕捉,那么第一辑“岁月寄怀”——尤其是作为全书“文眼”的《老屋和炊烟》一文——便是镜头向内的探寻,这是一个心灵的“暗房”,作者在其中,用时间的显影液,冲洗着关于“故土”的老旧底片。
摄影是“保存”的艺术,旨在对抗记忆的磨损和时间的重负,但作者开篇即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他所要保存的图景——“记忆中清水湖畔的老屋和炊烟”,已经“铁定不复存在, 永远地一去不复还了”,物理意义上的“根”已经断裂,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现实,一张曝光过度、几乎全黑的底片。
然而,显影的过程,恰恰是在这“不复存在”之后才真正开始,作者的情感需要一个新的附着体,一个永恒的“所指”。杨明强精准地找到了这个意象,他写道,“然而, 脑海中, 故乡清水湖畔的老屋, 尽管不再有袅袅炊烟, 但清水湖上生生不息的浩渺烟波, 却永远荡涤在我的内心深处。”这是美学上最核心的转折点,那缕人间的、温暖的“炊烟”,被作者在精神暗房中,奇迹般地升华为永恒的、自然的“烟波”,“炊烟”会散,但“烟波”永存。“烟”的意象得到了保留与延续,但其载体从脆弱的人造物,转变成了生生不息的大地景观。通过这次精神上的自我升华,杨明强的乡愁不再是一种面对失落的哀悼,而是一种寻得归宿的确认,他的“根”,从此不再扎根于那座终将风化的“老屋”,而是扎根于金银寨下、清水湖畔的“山水”本身,那片“魂牵梦绕的心灵净地”。
如果说“烟波”的意象是冲洗照片过程中的“显影液”,那么父母之逝便是那道“定影液”,文中那句沉痛而通透的感悟:“常言道: 父母在, 人生尚有出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正是这场精神显影的最后工序,父母的离去,合上了他返回现实世界老屋的出处,迫使他必须确认那条精神的归途,这条归途,则最终定影在清水湖的“浩渺烟波”之上——这是一场内观的心灵显影,是一次从“出处”到“归途”的精神之旅。
以“白描”定格人间
从广角的“观景器”到内观的“暗房”,杨明强先生的镜头最终转向了具体的人。在第五辑“礼敬达人”中,他展现了作为“摄影化诗学”的第三重境界:出神入化的焦点式白描。这种“白描”,在摄影的语境中,就是“肖像摄影”,这是一种高光圈、浅景深的笔法:背景被诗意地虚化,而人物的神采则被锐利地凸显出来。
这种能力,无疑源于杨明强先生40年的媒体生涯。请看他为奇人阿年定格的“焦点”:“秃头光亮, 戴副眼镜, 方格短袖, 中等个头, 一副老顽童派头和装扮的阿年……”再看他为邓义初老校长捕捉的神韵:“邓老个头不高, 虽头发花白, 却面色红润, 神清气爽。……总爱穿着一身素净、整洁的休闲装, 言谈随和, 亲和力强, 颇有学者风范, 没有半点儿‘官架子’。”这些描摹,没有繁复的修辞,却充满了精确的信息量和生动的画面感,“秃头光亮”与“方格短袖”勾勒出阿年的不羁,“个头不高”与“面色红润”“素净休闲装”则传达出邓老先生的谦和与厚重。在《〈大熊猫图志〉引发的故事》中,这种焦点技艺更是炉火纯青,他通过对胡锦矗、秦自生教授等学者的白描,将人物勤勉清正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杨明强用最精炼老到的笔墨,以近乎“抓拍”的速度,定格了这些可敬可爱之人最生动的灵魂的剪影,他的笔触如同摄影师的对焦环,总能准确地聚焦人物精神特质,从而完成一次次深刻的文学造像。
纵览此书,我们看到了一条清晰的脉络,杨明强以他跨越教育界、新闻界和文艺界的独特人生阅历,将他作为媒体人的客观之眼、摄影家的审美之眼,与作家的人道悲悯之心,熔冶于一炉。这部散文集,是他40年行走、观看与思考的影像画廊,也是他坦诚记录一个文化学人心路历程的心灵底片。
法国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曾提出“决定性瞬间”,杨明强的这部散文集,就是他这闳中肆外、沉潜笃行生涯的一个“决定性瞬间”。最高明的文学创作一如最高明的摄影技术,它所定格的,不仅仅是外部世界的云影天光,更是作者内心的那片心灵净地上,永不熄灭的璀璨灵光。(作者:许淳彦)
编辑:王欣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


天府书展|当阅读走出书页,“安逸四川”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天府书展|三地联动、微剧破圈!“文化名家采风行”启幕,四川文旅融合探索新范式

天府书展|阿来与乔叶,带我们走向诗与远方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