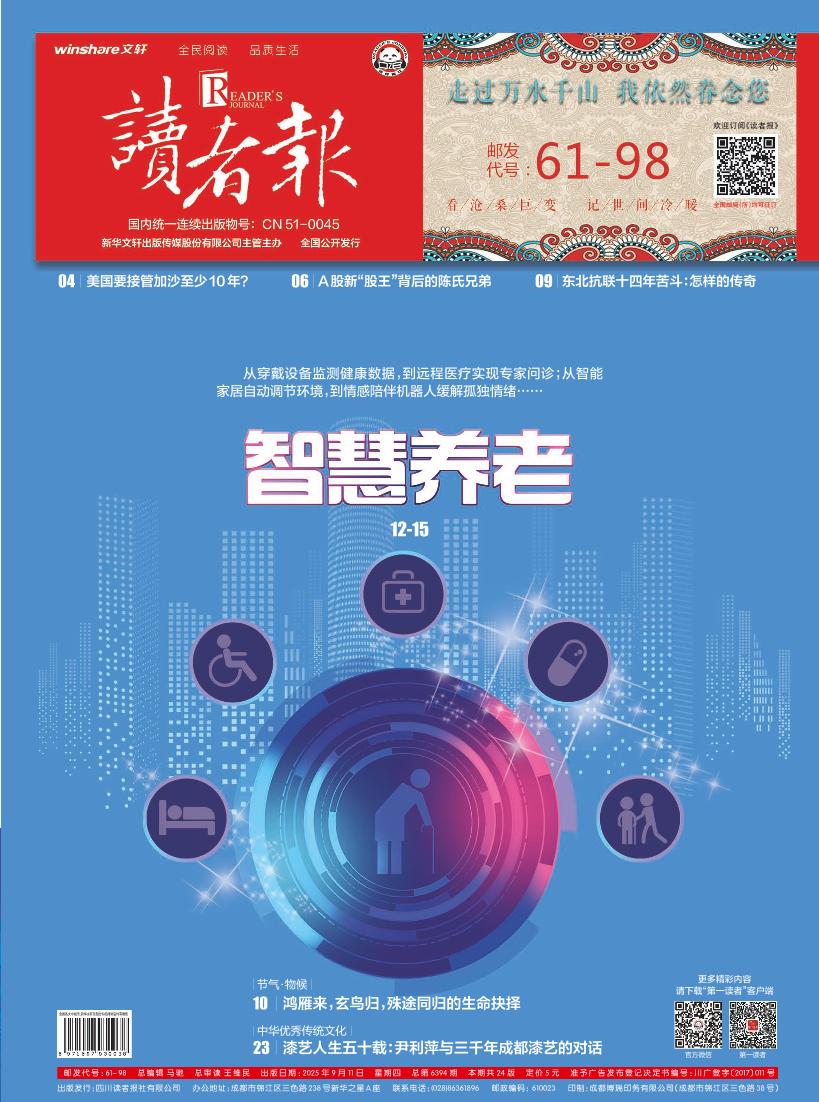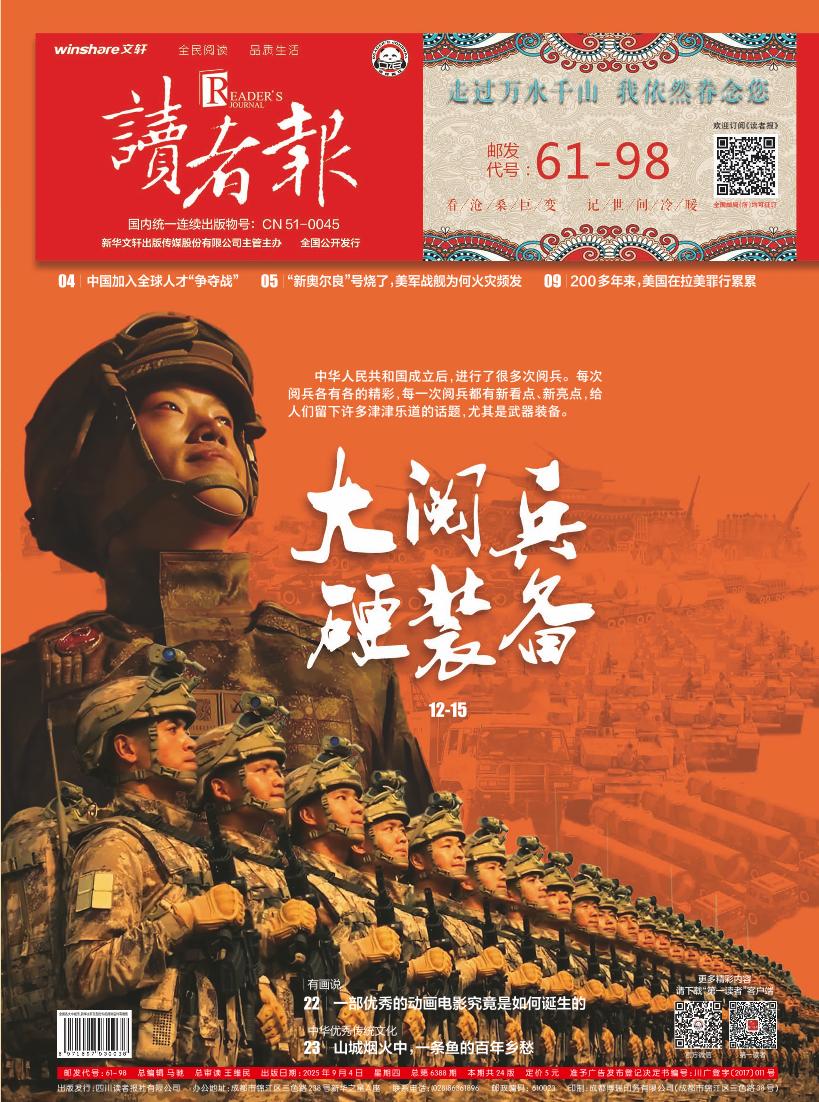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日前,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都江堰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市文联副主席王国平主编的《随喜帖——李铣诗歌评论集》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这部收录了20余件评论文章、4件人物印象记、65首诗作及5篇诗歌思考短文的集子,不仅成为解读诗人李铣的“密钥”,更以多维评论视角,接续了成都、四川作为诗歌重镇的传统脉络。正如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梁平在序言中所言:“如果把李铣的生命版图划分为生活场域和精神场域,他的精神场域就是他的诗歌。这两个场域可以划分,又是合二而一的,构成了他完整而丰富多彩的生命轨迹。”这种“双重场域”的融合,既是李铣诗歌的核心特质,也是《随喜帖》通过评论实践所构建的诗学图景——它让“人间烟火”与“思想光芒”在文本中对话,让个体创作与地域传统在评论中共振。

●“随喜帖”的内涵:“文朋诗友们之间的情谊”
相信很多人拿到《随喜帖——李铣诗歌评论集》这本书时,对书名中的“随喜帖”有点懵。其实,“随喜”一词,“本佛家语,谓见人行善,随而生欢喜心也。”(文学史家王季思先生语)王国平则进一步解释道,具体到这本书,“随喜帖”实际上是代表着文朋诗友们之间的情谊,就是大家读了李铣的作品之后的感悟,甚至顿悟,而随手写下来的一些心得体会和感受。
李铣是谁?李铣,土家族,祖籍重庆秀山,生于四川成都。20世纪80年代初在成都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曾参与成都大学、红杏诗社、萤诗社、成都市文化宫、星星诗刊社等单位、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的诗歌活动,至今活跃诗坛。作品发表于《诗刊》《星星》《十月》等报刊,收入《中国年度优秀诗歌》《中国年度诗歌精选》《四川百年新诗选》等选本。著有诗集《感动》《歌声从天而降》《月亮上有水》《赴永远的远》等。作品曾获首届金芙蓉文艺奖、首届李劼人·锦水文学奖等表彰。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成都市文联第五届全委会委员、四川天府新区文联常务副主席。
李铣从事诗歌创作40余年来,收获诗歌500余件,同时也收获了朋友们对他诗歌评论的文字随喜。本书收入了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木斧、尚仲敏、李自国、龙郁、宫白云、何光顺、李永才、陈小平、凸凹、唐宋元、王学东、肖云、林科吉、雪峰、吕历、赵学诚、龚学敏等评论文章20余件,对其诗歌进行了细致解读,分析了其诗歌主题、语言、技巧之得失,并对其诗歌风格的形成进行了科学梳理。该书还收入马及时、何民、陈晓兵、王国平撰写的人物印象记4件,对日常生活与烟火人间中的李铣进行了诗意表达与原生态呈现。同时,书中还附录了李铣旧作《栀子花开》《杭白菊》《歌声从天而降》等33首,新作《流水渔樵》《美好的仍然是离愁》《雨季奔波》《灵岩书院》《看戏》等32首。李铣关于诗歌的思考短文《我相信月亮上有水》等5件,可以帮助读者认识一个更加立体、生动、丰满的诗人形象。
 ▲诗人李铣
▲诗人李铣
●双重场域的诗性融合:李铣诗歌的基因与表达
李铣的诗歌从来不是孤立的文字建构,而是其生命轨迹的诗性投射,这种投射既扎根于具体的生活场域,又升腾于超越性的精神场域。王国平在《歌声从天而降,诗意破土而出》中敏锐地捕捉到李铣的“家学基因”:祖父李亨“关注民生、着眼教育、务实求新的历史责任感”,父亲李绍明“道德、文章堪称楷模,学术声望名播天下”,这种“勤奋认真、有责任感、诚恳、执着”的品质,“在他的生活、工作与诗歌中一样都没有落下,随处可见”。而成都大学时期的师承更赋予其文学底色,李铣在《我相信月亮上有水——〈月亮上有水〉后记》中坦言,古典文学老师白敦仁、钟树梁、谢宇衡与文学概论老师钟文的教诲,让他“传统文化功底与新文学理论齐头并进,成为支撑他三十多年来文学创作与工作的两大基石”。
生活场域为李铣的诗歌提供了“人间烟火”的底色。他的诗从不回避日常的琐碎与温情,如《母亲老了》中“母亲老了/走着走着/像个小孩/突然跌倒//小孩跌倒/一跃而起/母亲老了/爬不起来了!”,王国平评价这类诗句“没有任何修辞手法……那些朴实的句子中仿佛有一把刀子,戳痛我的内心”。这种对生活的“原生态呈现”,在陈小平看来,是“寻找镶嵌在琐屑日常生活缝隙中的诗性”,他以《清漪》为例,“‘一杯酒的生活/无关你我酒量的大小/是酩酊大醉或浅尝辄止/只要我们围坐一起/感情的浓度就胜过酒精’,这种朴素,一方面体现在他的诗歌更多地写到的是他生命中的人,比如恋人、妻子、父母、朋友,还有他自己,这让人从他的诗歌中真切地体验到生活的具体与实在”。
而精神场域则让李铣的诗歌拥有“思想光芒”的高度。他在《诗魂附体》中直言,诗歌创作的初衷是“孤独感触发了我强烈的表达欲望”,但随着创作深入,他开始“更加关注人生、人性、人心和人的命运,力图从个人生活的立场和认知去解读人类的终极问题,打捞一代人的集体经验与记忆”。这种对终极问题的追问,在《去往或者回归》中具象化为“回形针似的道路,别一束格桑花,通往/并不遥远的溜溜城池”,梁平认为这“回形针”是“鲜明而强烈的印记”,“格桑花”是“实实在在的美好”,“溜溜城池”是“梦幻般神秘的召唤”,而“无论去往或者回归,人生的道路都不过如此。曲折、艰难,循环、重复,但是只要心里有梦、有美好的指引,就能义无反顾,一直走下去。这是李铣精神境界的另一种坚韧,也是认识李铣其人其诗的密钥”。
值得注意的是,李铣诗歌的双重场域并非割裂,而是“合二而一”的融合。他在《关于诗集〈赴永远的远〉的随感》中提出“‘美即是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换言之,作者所经历的自然与社会、人与事、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等等,都将在作品中曲折表达,光彩熠熠”。这种“生活”与“美”的统一,让他的诗既能“以‘诗’捕捉与打捞有爱、有泪、有感情的日常生活”,又能“让自己的‘思’沿着升腾的泪水不断飞翔,抵达遥远的天际,继而仰望星空,最终以巨大的包容和悲悯俯视人类,鸟瞰大地、观照内心”——“人间烟火在下,思想光芒向上”,恰是对这种融合最精准的概括。
 ▲2022年5月14日,李铣《赴永远的远》凸凹《水房子》读者见面会合影。
▲2022年5月14日,李铣《赴永远的远》凸凹《水房子》读者见面会合影。
●多维评论的共振:《随喜帖》对李铣诗歌的解码
《随喜帖》的价值,不仅在于收录了李铣的诗作与思考,更在于它汇集了不同领域评论家的声音,形成了对李铣诗歌的“多维解码”。这些评论既从语言、哲学、地域等角度切入,又通过“诗说”“诗相”等板块,构建起李铣诗歌的立体形象。
在语言与哲学维度,评论家们共同捕捉到李铣诗歌的“进阶性”。诗人、诗歌评论家、四川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尚仲敏指出,李铣近年的创作“进入了更接近诗歌本质、更高级的第二阶段。那就是他发现了‘语言之美和哲学之美’……李铣从‘咏物感怀’直达语言的内核,在词语、意象、人物、事件之中,依靠高超的技艺,呈现了语言之美。同时,又给我们展示了他的哲学思考”。诗人、四川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木斧则以“简洁、清新、明朗”定义李铣的语言风格,“读他的诗,便看见了一掬又一掬波动的水,一弯又一弯折射的星光,一缕又一缕生活的乐趣,一首又一首感情充沛的诗”,他以《车过宝鸡》为例,“‘突闻一阵马蹄声响起/犹如疾风,追着奔驰的列车古陈仓道上/擂动蜀地的战鼓也传来中原的气息’,马蹄声响,一晃眼,八百里秦川从眼帘中跑过去了,不仅写了速度,而且包含了古今”,认为这种“大写”手法“不得不叫人另眼相看”。诗歌评论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何光顺则从哲学层面解读,“李铣的诗,就如高僧参禅,参悟出人间因缘,烛照出动静变化里的幻有。他写出人生如寄的美丽,写出古老祭奠里的深沉,写出城墙剥落里的历史回音,那胜利和失败,那岁月和伤痕,那梦里的忧郁和冷冷的雪,那从外来的节日里我对故乡村庄的回返,都无不显示出一个经历着风霜的男子汉对于生存的思索和探照。”
在地域文化维度,诗人、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星星》原主编龚学敏的评论揭示了李铣诗歌的“在地性”。他认为“李铣的诗中,我们除了能够读到他对自然山水的诗意描写,还能感受到他对四川地域文化和悠远历史的深入挖掘与独特的展现。不仅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地域文化的窗口,更能引发出我们对身处地域的多维思考”。这种“在地性”并非简单的地域符号堆砌,而是融入情感与记忆的文化表达——正如李铣在《我相信月亮上有水——〈月亮上有水〉后记》中回忆的,红杏诗社、“萤”诗社的经历,让他的诗“与成都的诗歌传统深深绑定”,而诗人、儿童文学作家马及时在《李铣与那些难忘的诗歌往事》中记录的都江机械厂单身楼岁月,“几个年轻人常常彻夜长谈诗歌,为北岛、顾城、舒婷倾倒,为叶文福、骆耕野燃烧”,更让这种地域文化有了温度。
“诗相”部分的人物印象记,则为评论提供了“生活视角”。陈晓兵《风雅框架——李铣其人其诗》、何民《朋友李铣》、马及时《李铣与那些难忘的诗歌往事》、王国平《歌声从天而降,诗意破土而出》四篇文章,跳出文本分析,从日常生活切入,展现了“温文尔雅”的李铣——他会“拉住张庆、廖永德、何民、汪浩和我说:‘走,再去喝一会儿茶,我新写的几首诗请大家提点意见’”(马及时),也会在廖永德去世后“四处奔忙,联络了成都市和其周边区县的老师及诗友……一起悼念永德并挥泪写诗作文”(马及时)。这种“生活化”的描写,让李铣的诗歌形象更立体——他的“思想光芒”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源于对生活的真诚;他的“人间烟火”也并非琐碎堆砌,而是饱含对人的悲悯。

●评论的在场意义:《随喜帖》与成都诗歌传统的接续
王国平坦言,主编《随喜帖》的初衷,是“尽管成都拥有如此众多的优秀诗人,但目前对诗人们的研究还不是很丰富。因此,希望通过《随喜帖》对李铣作品的剖析,让更多人关注李铣的诗歌,关注成都的诗歌,更期待该书能助力成都乃至四川诗人的作品研究工作。”从这个角度看,《随喜帖》的价值早已超越对李铣个体的评论。
成都历来是诗歌重镇,“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成都诗人叶伯和、周太玄、王光祈、巴金、艾芜和流寓成都的诗人何其芳、臧克家等创作了大量新诗,推动了新诗早期的发展。新诗诞生一百年来,成都始终是与北京、上海比肩的诗歌重镇,涌现出了杜谷、王尔碑、流沙河、木斧、孙静轩一大批重要诗人,为中国诗坛贡献了诸多优秀文本”。李铣作为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其诗歌的“双重场域”恰是成都诗歌“现实关怀”与“精神追求”的延续——从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到李铣的《灵岩书院》,从木斧的激越到李铣的沉静,成都、四川诗歌始终在“人间烟火”中坚守“思想光芒”。
《随喜帖》的评论实践,更为成都诗歌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它没有采用单一的评论视角,而是汇集了诗人、学者、评论家的多元声音——既有梁平、木斧等资深评论家的宏观把握,也有宫白云、李永才等中青年评论家的微观解读;既有对诗歌文本的分析,也有对诗人生活的记录;既有对个体创作的评论,也有对地域传统的梳理。这种“多维评论”模式,不仅能更全面地解读诗人,更能为后续的四川诗人研究提供借鉴。正如李铣在《诗魂附体》中所言,“诗是文学巅峰上的明珠,永恒地辉耀世间,就像幽魂附体,引诱众生攀缘采撷……如此形成的人文路径,构筑了社会历史的重要情感存在,直击人类心灵的柔软,使生命具有了神圣而神秘的意义”,正是对这种“人文路径”的守护与传承。
此外,《随喜帖》还通过收录李铣的“诗想”与诗作,构建了“诗人自白—评论解读—文本呈现”的完整链条。读者既能通过李铣的《赴永远的远》自序、《我相信月亮上有水》后记等文章,了解其创作理念;也能通过评论家的文章,深化对文本的理解;更能直接阅读《栀子花开》《流水渔樵》等诗作,形成自己的判断。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让评论不再是孤立的解读,而是与诗人、文本的对话——它让评论“在场”,也让诗歌“永生”。
《随喜帖》以“随喜”为名,既承载着“文朋诗友们之间的情谊”,也暗含着对诗歌的敬畏与热爱。它通过对李铣诗歌“双重场域”的解码,不仅让我们认识了一位“人间烟火在下,思想光芒向上”的诗人,更让我们看到了成都、四川诗歌传统的生命力。尤其是《随喜帖》的评论建构,是认识成都诗歌,乃至中国新诗“现实关怀与精神追求”的重要窗口——它让我们相信,在浮躁的时代,诗歌依然能在“人间烟火”中升腾“思想光芒”,评论也依然能在对话中守护诗性的在场。(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王欣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


“阅读+”新形态⑤丨阅读新“视界”:当科技与书香共舞

“阅读+”新形态④丨书香里的成长方程式:文轩亲子书店的服务赋能之路

“阅读+”新形态③丨水下书店的诗意栖居:当阅读遇见公园城市的生态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