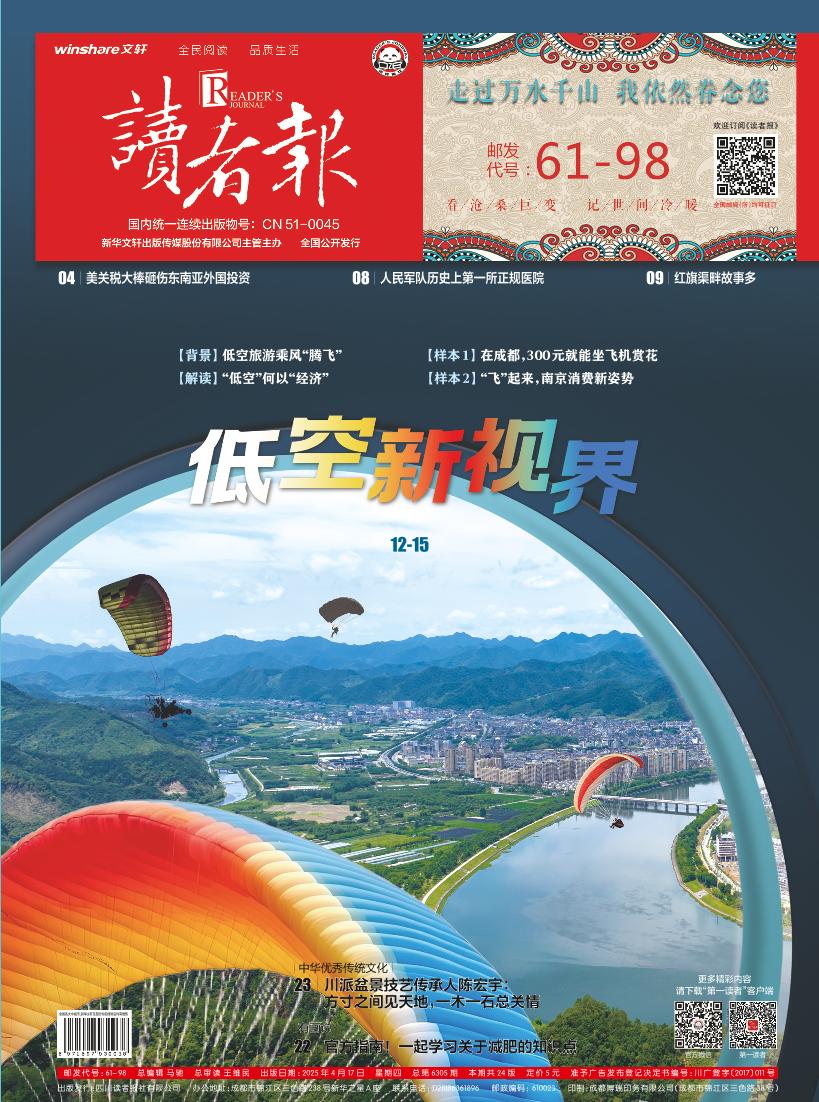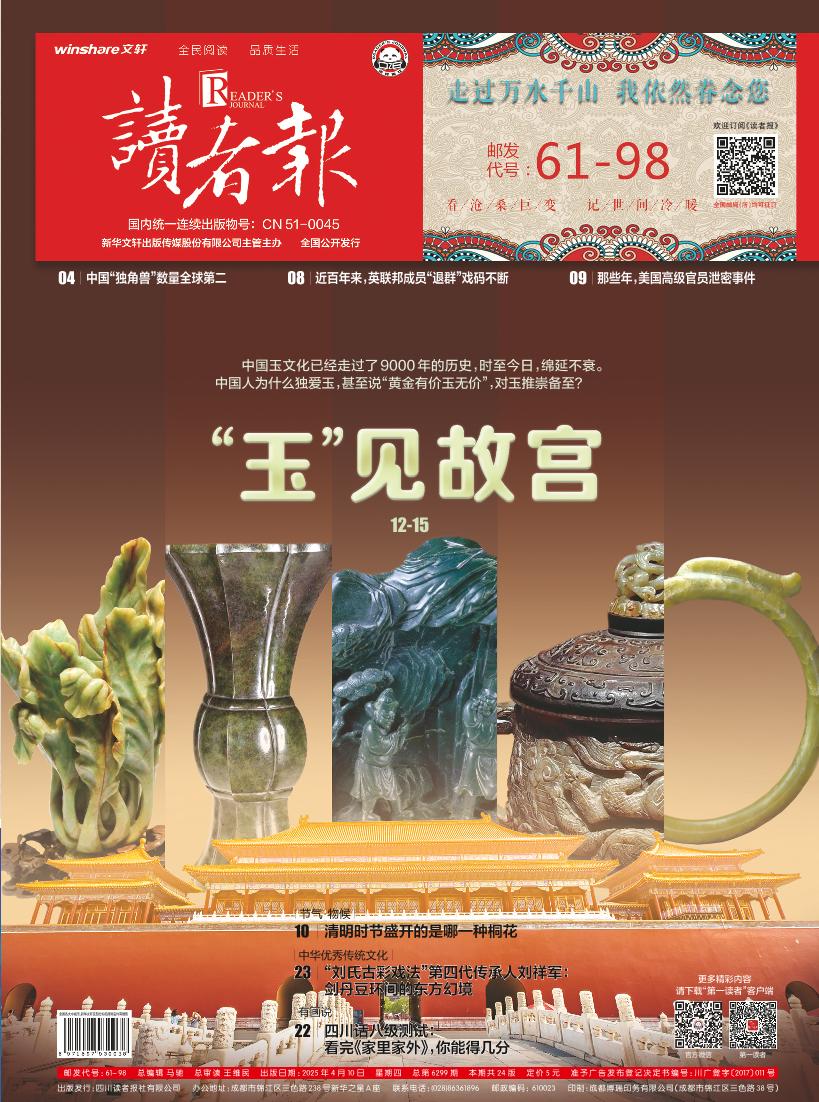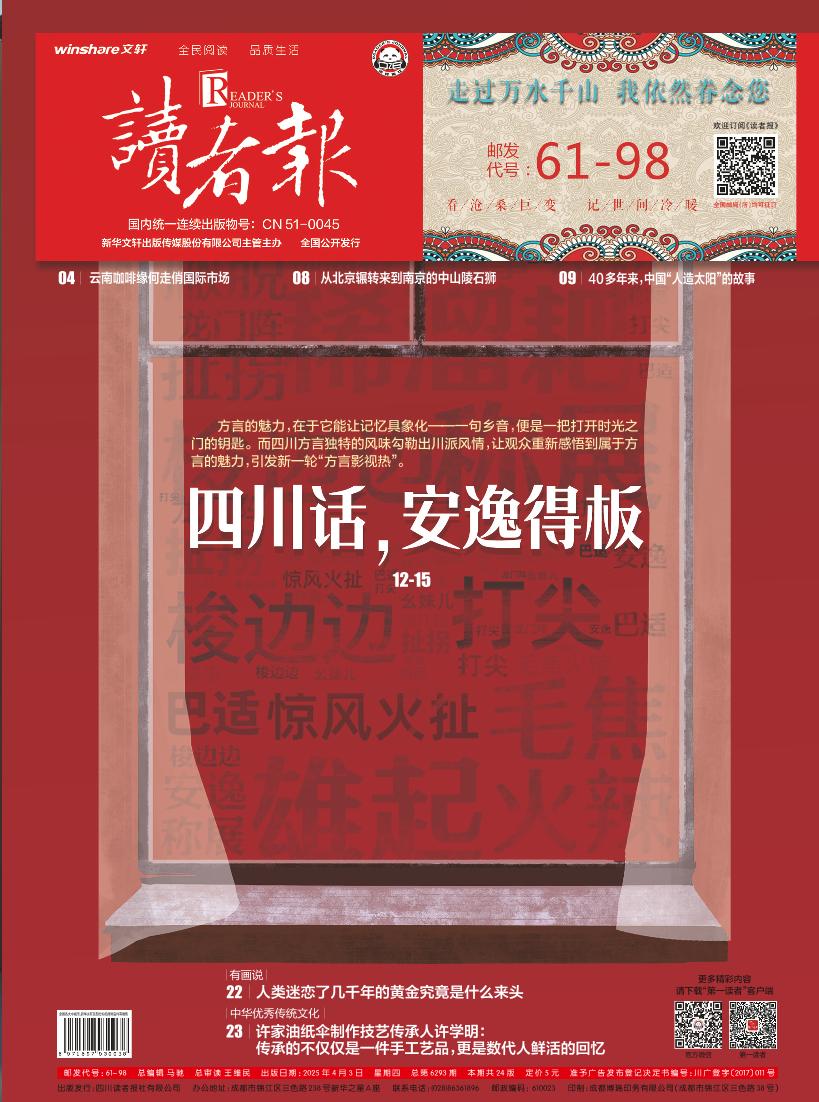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文轩全媒体服务平台
本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严禁处理、传输国家机密
2025年的春天,宛如一只轻柔的手,总在叩击记忆的窗棂。时光匆匆,马老离开我们整一年了,然而,那些与他围炉夜话的往昔片段,犹如三维全息影像在记忆空间次第展开。
犹记得他104岁封笔之际,那颤抖的手在《夜谭续记》的扉页题字的剪影,宛如一幅岁月沉淀的画卷。还有109岁高龄时,他撰写的回忆性文章《钱瑛,我的引路人》(《随笔》2023年第4期),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钱瑛同志对他的革命启蒙与人生指引。文中,他亲述《国际歌》唤醒信仰的往事,每一个画面,都仿佛被理想主义者的炽热与文人风骨的清辉所浸染,熠熠生辉。
国际悲歌歌一曲
回溯到1938年湖北省委七里坪破祠堂的那个星火之夜,斑驳的土墙上,钱瑛同志用俄语高唱《国际歌》,这歌声宛如一道永恒的印记,深深地烙在了马老的记忆深处。那一夜的火光,透过祠堂的裂隙,将“英特纳雄耐尔”的铿锵韵律,熔铸成了革命者心中坚不可摧的精神钢印。马老向我描述时,他那原本浑浊的瞳孔,仿若突然迸发出星辰般璀璨的光亮,说道:“她唱得像准备走上刑场一样。”这束穿越了86年时空的光,让我仿佛看见,在战火纷飞中,《国际歌》的俄文原版与中文译本相互交响,这不仅仅是国际共运的史诗回响,更似一个民族在寻找精神原乡的悲壮跋涉,犹如夸父逐日般充满着坚定与执着。
信仰,往往在淬火时刻得以彰显。马老轻叩桌面,呷一口清茶,缓缓说道:“从入党的这天起,我改名了。”那袅袅升起的水雾中,仿佛浮现出何功伟夫妇就义前的最后对视。当叛徒的枪声撕裂鄂西的晨雾,他蘸着血泪写下“夜半歌声惊鬼神”,但在组织纪律面前,却化作清江壮歌中“血泪凝成字字真”的隐忍。这种革命者的思念,犹如松柏在寒冬中的坚守,是枪林弹雨中对同志的牵挂,是牢狱绝境里对信仰的执着坚守。文章不仅是对钱瑛的悼念,更揭示了老一辈革命者“一诺千金”的精神内核——从入党誓词的践行到毕生理想的坚守,钱瑛的教诲始终是马识途的人生坐标。就像“《盗官记》结尾那句振聋发聩的宣言,‘农民必须要有最先进政党的领导!’”马老说:“她的形象如洪湖的波涛,永远激荡在我的心中。”这无疑是对其革命信仰的有力呼应。
马老曾身为地下工作者,他巧妙地将革命者的使命感融入创作之中。他书中“太阳底下无新事”的隐喻,恰似一面古老的铜镜,在当今社会依旧具有警示价值。例如《买牛记》揭露的贪腐问题,《亲仇记》呈现的底层疾苦,如同镜子一般与当代社会形成映照。他通过《夜谭十记》构建的“历史——现实”对话,既是对旧时代的诀别,也是对未来的期许。这恰似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唯有坚守信仰、不忘来路,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书中“冷板凳会”的设定,既是对民间智慧的致敬,也暗含革命者潜伏时的生存智慧——通过“摆龙门阵”传递信息、凝聚力量。这种创作视角使作品超越了简单的讽刺,成为革命年代的精神镜像。《夜谭十记》1982年首版即印20万册,印证了其“文字不朽,精神永存”的预言。
马老以文学为笔,记录革命历史,强调革命精神和民族英雄的重要性,这种跨越时空的革命共鸣,犹如一条坚韧的丝带,成为历代共产党人的精神纽带。他曾在自寿诗中写道:“老来自诩识途马”,并将书斋命名为“未悔斋”,此名取自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其中蕴含着他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这份初心就像一颗璀璨的星辰,贯穿了他的一生。
78年文脉长跑
2010年冬夜,95岁的马老在癌症病榻前摊开稿纸。从1942年构思到2020年付梓,《夜谭续记》的30万字手稿在消毒水气味中生长,如同三星堆青铜器穿越时光破土而出。散发着古老而神秘的气息。马老始终秉持着文学应“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理念,用通俗的语言传递崇高的理想,坚决抵制低俗化倾向。文学界将《夜谭续记》视为马老百年文学生涯的封笔之作,它承载着深刻的历史情怀与文学坚守,宛如一座文化的丰碑。
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接过这部承载着与“韦君宜的世纪约定”的作品时,他们触摸到的不仅仅是文字,更是一位革命者、知识分子对文化契约的坚守,如同古代文人对“一诺千金”的执着。
在与马老交往的过程中,我们有着数不清的龙门阵可摆。当然,每次都是他主讲,每次都有新话题,时间也控制在1小时内,其中《夜谭续记》“摆”的次数较多。
《夜谭续记》是马识途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韦君宜近40年的创作约定。1982年《夜谭十记》出版后,韦君宜提出延续“夜谭文学系列”的构想,希望他用文字记录其“亲历或见闻过许多奇人异事”,但因故中断。直到2010年电影《让子弹飞》带火原著,95岁的马识途毅然重拾笔杆,在癌症治疗期间带病创作,以“司马迁写《史记》”的毅力完成初稿,104岁正式封笔。这种跨越时代的信守,彰显了革命者对理想的执着与文人对文学的虔诚。他曾反复对我说,《夜谭续记》的问世就是源自这样一个“承诺”。过程中,他多次问我,这样的通俗文学在当今有无价值?有无市场?年轻人是否喜欢?水平会不会低于《夜谭十计》等等。其实,这些问题在他的《文学三问》一文有明确的解答。
《夜谭续记》完稿后,我有幸成为先人一步的读者。一天,马老将30多万字的文稿录入一台老式陈旧的电子阅读器交给我,这台机器伴随马老多年,他说用顺手了,还能用就不必更换。他让我先看,并提出意见。在阅读器上看文字,虽费眼力,但文字流畅,故事曲折精彩,好看,我一连读了三遍,兴奋不已,兴致勃勃地前往指挥街省人大宿舍马老家中。我从兑现承诺的文学担当,民间立场的叙事坚守,幽默背后的现实关切,生命力的文学见证,文化传承的自觉实践等五个方面对作品作出判断:
作品延续《夜谭十记》的“龙门阵”形式,以四川方言讲述从民国到新中国的市井故事,聚焦普通人的命运浮沉。如《玉兰记》描写女大学生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重逢记》呈现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羁绊。马识途通过“民间性”视角,将宏大历史拆解为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既呼应了“新社会也有新故事”的时代命题,也延续了四川文学“地方路径”的传统。
我以为,与他早期作品的讽刺风格不同,《夜谭续记》的叙事更趋质朴。马识途以“茶余酒后消磨时光”的闲谈姿态,包裹对权力腐败、人性异化的深刻洞察,延续了“虽不足匡时救世,却可延年益寿”的创作哲学。在《玉兰记》《重逢记》的四川方言叙事中,马老将“摆龙门阵”升华为对抗遗忘的武器。那些浸润着盖碗茶香气的市井故事,既是“冷板凳会”的现代变奏,方言里的精神原乡,也是对官方话语体系的柔性制衡。正如他在《封笔告白》中所言:“盐味的俗文学观,才是民族文化的DNA。”
这部作品以106岁高龄完成,创下中国作家创作年龄纪录。从1942年首次构思到2020年出版夜谭系列第二部,历时78年,历经三次书稿损毁仍坚持创作。正如马识途在《封笔告白》中所写:“无愧无悔犹自在,我行我素幸识途”,其“勤用脑,多思考”的长寿秘诀与文学热忱,体现了对生命意识与文化传承的执着,共同铸就了跨越世纪的文学丰碑。马识途将《夜谭续记》视为对巴蜀民间文化的抢救。书中大量使用四川方言和民俗元素,如“摆龙门阵”“盖碗茶”,既是对传统说书艺术的致敬,也通过“秦局长”等角色暗示民间叙事对官方话语的平衡。这种“盐味的俗文学观”,成为当代文学民族化探索的重要实践。
听罢,马老沉思了一会。忽然,他说,“丹枫啊!你是我的知音!你的鼓励,坚定了我的信心。”马老一句话,让我心跳加速,血压上升,有些不安。我急忙回应,这是您的历史担当,文化自信,笔尖上的精神传承。随后我们又从一些细节、语言、人物等方面交换意见。我建议马老,尽快找到帮手,协助修改文稿。万梅姐和高虹有幸被马老选中。万梅姐是马老的二女儿,陪伴照顾老父多年。朝夕相处,耳闻目睹,家学浸染,自身热爱相加,具有相当的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准;高虹曾是《四川文学》的执行主编,她们为《夜谭续记》锦上添花而婉拒名利。
分别时,我对马老说,这本书稿不仅是您生活的汇集,更是您人格魅力的展现。作品中蕴含的生命力量和思想深度,是对读者的一种鼓舞和激励。他颌首微笑。
马老为此专赠书法“高山流水觅知音”一幅,嘱我饰壁。我喜不自禁,把它当成宝贝珍藏。连声说道,这是您发给我的“福利”啊!
有人说时间会磨平人们的棱角,信任是彼此之间的核心。是的,岁月让我们有机会分享彼此的人生经历、观念碰撞,在共同的话题中,深化了我们忘年交之间的友谊。也正是在这种信任中,我们更加愿意敞开心扉,分享彼此的困扰与担忧。这种信赖感让我们在交往中更加自由、轻松。定期与马老交流成为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马老说,我很珍惜这种难得的忘年交,我答,它成为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常常展纸回味,字中真意真情让我明白,这种关系不仅让我感受到世界的温暖,更让我在成长道路上获得指引和力量,它成为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
未曾完成的心愿
书稿完成了,在出版社的选择上,我和马老有些“分歧”,相互说服对方,一度形成“拉锯”。主要面临“省域出版”与“京城落户”的抉择,我希望留在本省,他认为放在北京。我据理挽留的理由是,本着巴蜀故事、四川精神、本土作家写作,省内出版较为妥当。他尽力说服的缘由为,“虽然还有很多遗憾,也算完成了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定。跟韦君宜的约定,总算完成了。”他抚摸着书稿上的折痕说,“待书出版,我还要在图书扉页上写了一段话:谨以此书献给曾首创‘夜谭文学系列’并大力推出《夜谭十记》一书的韦君宜先生,以为纪念。”马老多次讲起,他与中国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往事和友谊。随着交流的深入,我愈能理解马识途对朋友的真诚、对情义重如山的情怀,我被感动了,欣然放弃了“地方保护主义”。我以为这部书若在国家级文学出版平台出版,可以见证马老百年人生铸就的文学引力场:革命者的热血与文人的风骨在此叠加,地下工作者的机敏与小说家的诙谐在此纠缠,夜谭续记的幽邃与龙门阵的鲜活在此共生,在出版物中完成历史褶皱里的人性显影和独特文化的精神编码,岂不是更有意义。这不是地理位置的选择,而是文明坐标的校准。马老多次说我懂他。
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接过这部践“与韦君宜世纪之约”的书稿,触摸到的不仅是巴蜀方言的韵律密码,更是革命文人对文化契约的矢志守护。恰如邵荃麟当年鼓励马老业余创作等于把生命延长一倍。而他多次提及我的理解和支持,帮他完成了这桩心愿!
《夜谭十记》出版,好评如潮。他通知我去家取书,在扉页上签赠"朱丹枫老友正之"时,他手腕颤抖在宣纸上晕染出独特的笔意。我又拥有了一本马老亲自签名的赠书。
那天,恰巧收到华西医院的体检报告“肿瘤阴影烟消云散”的医学奇迹,与他“与癌症赛跑”的创作姿态形成奇妙互文——真正的战士,连死神都要为之让路。他自豪地宣告:“咋个,病魔和我斗,落荒而逃了吗?!”继而,他坚定地讲:“一个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必须经过折磨,必须经过困难,没有经过磨难,要想成功一个什么事情,办不到的。”在《夜谭续记》后记中,马老感慨,一个人只要不怕死,便会勇气百倍,一有勇气,更有力量战胜危险和痛苦。
书的出版后,马老又约我再聊《夜谭新记》。这是夜谭序列的第三部,又有10个未及展开的故事装在他的肚子里了,如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残梦遗珠。我太佩服老人家了,他积累的素材多多,一薅就见到金山银山。他简直就是生命不息,写作不止;他在与时间赛跑,与癌症搏斗,与命运抗争。当时,鉴于他正全神贯注地打理《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我们商议,待该书出版后,再行《夜谭新记》的创作,我期待他永不停歇的笔锋再续“夜谭”佳话,我向他申请还作第一读者。他却说,我的书少不了你的“慧眼”,要搞好。这一搁,就再也没有捡起来。这竟成了终身的遗憾。
马识途的一生,是革命者、作家与文化传承者的三重身份的交织,其深情厚意既是对“新中国”沉甸甸责任感的回应,也是对民族精神不灭的坚守。他用一生诠释了对信仰的赤诚、对人民的深情、对历史的敬畏。既体现在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也融入了文学创作的字里行间。他的著作恰似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位百岁老人对家国、对战友、对理想的永恒眷恋。读他,思念如绸,缠绕在心头。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但《马识途文集》的“龙门阵”仍在摆,马识途以百年人生书写的不仅是个人传奇,更是中国知识分子“文以载道”的精神图谱——在嬉笑怒骂中坚守良知,在历史褶皱里打捞人性微光。他的文字是穿越时空的思念之歌,如同永不熄灭的灯塔,指引后人前行。将永远回荡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原野上。
再次来到“未悔斋”,书桌上的笔依然泛着温润光泽。这支记录过《马识途文集》深邃厚重、赤诚血性与幽默诙谐的“思想武器”,此刻正与墙上马老手书的“无愧无悔,我行我素”遥相呼应。我仿佛看见百岁老人伏案疾书的身影,听见他对未来的殷切嘱托。我忽然明白,当人工智能开始解析三星堆青铜纹饰的宇宙讯息时,马识途以百年生命书写的中国故事,正在元宇宙中生成新的文化亮点。既照亮历史深巷的斑驳苔痕,更指引着文明原野上的后来者。我忽然懂得:所谓缅怀,不仅是眼泪的祭奠,更是将精神火种嵌入时代基因的庄严仪式。
“未悔斋”里,永远有盏灯因他而明,为读者而亮。(作者:朱丹枫)
编辑:王欣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
一校:凌雪梅 二校:何建 三校:董小玥


2024“文轩好书”⑥|写了那么多年汉字,你真的懂汉字吗?

2024“文轩好书”⑤|你真的懂审美吗?在这里找到答案

2024“文轩好书”④ | 《蜀道十讲》:探寻蜀道文化的诗意与历史长卷